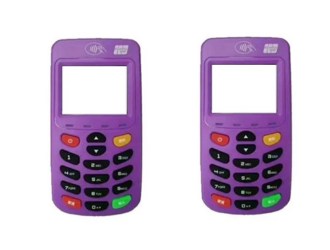網上有很多關于pos機銷售渠道,日本零售數字化為何仍靠POS機體系的知識,也有很多人為大家解答關于pos機銷售渠道的問題,今天pos機之家(www.shbwcl.net)為大家整理了關于這方面的知識,讓我們一起來看下吧!
本文目錄一覽:
1、pos機銷售渠道
pos機銷售渠道
作者:蕤內
出品:明亮公司
明亮公司之前連線了兩位在日本的投資人,從底層邏輯、消費人群、供給側探討了新消費與新品牌,他們分別是啟承資本在日本的研究員片矢東滋郎(東子)和“軟銀系”投資機構Z holdings的投資人李路成(Luke),兩位在消費和負責移動互聯網應用、數字化領域都有非常多的研究。
在此前的訪談中,兩位嘉賓提到,從底層邏輯來說,中國現在新品牌很少以品牌文化驅動,還是“賣貨邏輯”,處于增量市場的紅利階段。而當增量褪去,品牌開始找到自己獨特的價值主張,怎么說好品牌的故事,才是凸顯真正實力的時候。而在中國市場上部分面向年輕人的品牌,在日本也會有增長機會。不管在中國還是日本,對于容易“出軌”的消費者,快速迭代的產品仍十分有吸引力。
延續上次的話題,「明亮公司」此次對比了中日品牌和零售在數字化方面的區別,以及探討了中國品牌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定位、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上的問題。
過于強大的POS數字化系統
明亮公司主編:上次東子講到人群,即通過不同的渠道來去抓住不同的人群,是新品牌最大的其他機會,也提及了日本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產品牌興起的趨勢,有點像國內微信生態的微商。這么看,完美日記似乎有點像“微商3.0”,但它有用體系化的方式來做微信私域。
東子:對,即便是微商,也應該賣一些附加價值更高的東西。為什么?因為微商的銷售是基于人與人的信賴的。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些化妝品品牌其實都是以信賴為杠桿來去做高附加價值的,因為與消費者溝通越多,可以更容易賣更貴的東西。
之前我看了一個產品是專門賣女性的矯正內衣,半標準化定制,說白了是用人們的“自卑心”去做生意,這種企業把微商模式和BA(銷售助理)體系進行結合。通過培訓BA為前端的銷售專家進行獲客。這家企業一件內衣可能賣兩三千元,收入最高時大概有二三十億人民幣,百分之十幾的凈利潤。他們每年會舉辦姿態比賽,讓他們的用戶聚在一起,選出最有“自信”的那一個。使用的不是數字化的工具,但思路上則非常符合微商模式。
明亮公司主編:這個太驚人了,那現在日本有沒有新的工具類的平臺,或對品牌做數字化有貢獻的一些公司?
Luke:從投資的角度來說,結論上我們還沒有看到特別有殺傷力的工具出現。我們的觀察是許多的創業公司發現自己無法拼過大型平臺但同時又沒法做出商品價值更高的商品,因此他們現在還是更關注生產端的生意,比如給有意向做衣服的Influencer(意見領袖)賦能。
現在日本本土的創業公司中,出現了一批工具去幫助這些品牌的企劃者,創業者可以利用工具簡單地對接到設計師、工廠、倉庫等等。但是這些工具仍還不具備撼動市場的能力。
從品牌營銷工具的這個角度來說,被大眾認知和使用的目前可能只有LINE。不同領域的品牌有不同的痛點,然而疫情+廣告cookie規制嚴格化(廣告平臺的投放效果變弱)關鍵的問題變成了營銷線上化/電子營銷的效率化。廣告主從觸達率/轉化效果這些角度來考慮都會首選在LINE里制作“公眾號”,并同時結合其他廣告途徑去投放。
對比LINE或 Instagram。Instagram更偏媒體, LINE更偏CRM。品牌方在Instagram上會多進行增強品牌故事認知的照片投稿,以及粉絲獎勵活動。而LINE里有個叫open chat功能,用戶不用通過好友申請,會自發地針對品牌的話題進行“微信群“般的對話。同時很多品牌和用戶可以在里面直接交流。另外還有通過LINE 的機器人,類似于微信公眾號的自動回復,但會允許商戶開發直接在LINE完成購買。
明亮公司主編:有點像國內AI助手或AI客服,功能上也很像最近剛上線的微信客服,但是純基于文字的,它不通過語音方式。
東子:日本數字化做不好的原因,我認為在于日本last generation(舊世代)的體系過于成熟和強大了。
POS數據分析類似這種是NEC和7-11開發出來的。便利店的興起下,也誕生了一批新的品類,這些新品是靠POS數據探索出來的。比如伊藤園這個賣瓶裝茶飲料公司的轉折點,就是做為與便利店便當搭配購買的產品出現,在產品開發定義時得到了便利店的支持。部分零售商通過POS數據形成了從上游到門店端的閉環技術,實現了高效化。但這也提高了數字化難度。日本最近都在講DX(Digital Transformation),但就數字化的理解或應用程度上,還是離中國挺遠的。
Luke: DX是新冠疫情之后在日本開始火起來的詞語,因為疫情從物理上限制了日本從前習慣上使用人力去解決問題的習慣,倒逼社會反思日本各個層級的公司為何許多程式化的運營不能減少/使用外部的工具效率化。回到零售這個話題上,它是一個生態重構問題,供應/運輸/需求在現在的運轉模式下牽動著無數大中小商戶,并且他們已經有很成熟的方法論,比如利用POS機系統給出的市占率數據去分析自家商品的流通/滲透率,并進行改善。即便你告訴他們消費者線上的行為數據,第一他們沒有這個數據,第二他們即使能感覺到新數據的重要性也不懂怎么去運用。
明亮公司主編:日本品牌或零售渠道會特別強調流量這件事嗎?國內現在很多品牌模型會特別看重流量。
東子:日本畢竟線下更強大,所以核心不是(線上)流量,是線下的選址,所以更多是一個選址的生意。背景是日本的城市現代化和鐵路系統深深綁定,而鐵路系統決定了城市結構以及人流的屬性和方向。在日本,車站就是人流最大的商圈。日本線下業態的核心在于對人流的轉化。
明亮公司主編:中國和日本POS數字化最大的差別是什么?
東子:中國可能是全盤數字化了,日本可能是某些信息點的數字化。
Luke:關于日本POS機的系統數據,其實它們是非常孤立的。比如店鋪里的數據,賣了什么、多少錢,支付服務商是看不到的具體信息的。所以他們的數據運用非常局限,甚至他們也不知道消費者是誰。但國內可能消費者的ID下買了什么東西、花了多少錢,這些數據都有進行統合和分析,并反映到商品開發/運輸/銷售上。
東子:我記著,為了彌補POS數據的不足,日本有家折扣店上面全是攝像頭,記錄是誰在什么時候購買了什么產品。為了節省成本,這些攝像頭都是二手的手機,上面裝上他們自己開發的APP。
明亮公司主編:針對這方面的基礎設施沒有相應的供應商嗎?
東子:有的,但都還不夠成熟。這里有更多中國零售科技企業進入的空間。現在有幾家中國零售科技企業在嘗試進入日本市場,比如云拿科技。
明亮公司主編:說到數據孤島,國內因為電商或者互聯網平臺的頭部效應明顯,拿數據的能力比較強,但是跨平臺或公司也很難。這可能是中國現在前端的數據化做的好的地方,但在中后端的數字化還需要不斷建設。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電商先發展起來了,日本等發達國家先發展起來的是線下。
東子:這個還需要從歷史的角度簡單說一下。線下零售還是需要時間。日本第一個所謂的現代化零售企業“大榮”上市是1969年。這家公司是1957年成立的,1970年鋪到全日本,80年成為了日本第二家收入達一兆日元的企業(僅次于本田)。在80年代因為地價的上漲,他們開始轉型把店開在郊區。當時“大榮”的地位是“日本阿里”這樣一個角色,頂峰時期的并表收入大概2000多億人民幣。
我說的有些饒了。所以說日本的線下零售現代化從1945年開始,到了90年代末便利店模型的成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結束,花了45年時間。因為線下業態需要晚上,物流、選址、供應鏈等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行業人才水平的提高,時間周期漫長,受多方面外部因素的,并且是一個重資產的活。
明亮公司主編:中國以前很多品牌的“基礎設施”不由物流商、零售商去做,而是品牌自己去做,比如說礦泉水要賣到鄉、鎮一級的小店里,沒有零售商在那個時候可以下沉到鄉鎮,但是品牌有動力去整合資源,賣到更多地方。所以在整個定價體系里面,品牌有更大的話語權,他們有能力去跟零售商談賣多少錢,但國外零售商已經非常成熟了,基本購物人群都是從幾個大渠道里去消費,比如日本三大便利店。
東子:日本品牌很慘的,基本上都會生產Private Brand,給渠道品牌代工。
明亮公司主編:相當于品牌給零售商打工,整個價值中樞是偏零售端的?
東子:就是因為渠道太集中了,(品牌)變成供應鏈公司了,但品牌也不得不這么做。
如果品牌方不配合渠道商生產PB,渠道商會為了獲客把品牌做成引流款銷售,打亂品牌方的市場價格。所以這就需要品牌給零售渠道代工Private brand(渠道品牌),以保護自己的價格和銷量。如果被當作“引流款”銷售,那這個品牌的品牌資產會嚴重受損。日本以前就有一家規模遠比資生堂大的企業,因為沒保護好品牌資產,關注眼下變現,封死了自己高端化的道路。
明亮公司主編:在毛利凈利上會體現嗎?零售的毛利或它的零售終端的凈利大概能達到多少?似乎中國的消費品牌,低于50%毛利基本上就沒法做了,但線下零售公司(比如大賣場)的利潤率更低,凈利率大概也就1%-2%,不知道日本會不會更高一些?
東子:日本渠道凈利會高不少。全家應該是7%左右,但品牌方的毛利很低。比如日本烘焙頭部企業山崎面包,都是勉強不賠錢。渠道與渠道之間的競爭也很激烈,因為日本一個街口可能不止三個便利店,非常密集,所以只能去壓榨上游的品牌以及加盟商。
「國潮」是不是品牌?
明亮公司主編:有哪些方向是中國有、日本沒有的,但可能做出一點增量的?
東子:性價比型的產品在日本成功幾率更大,但是品牌類不太好說。因為非常依賴于創始人的價值感知。
品牌類的企業,我覺得機會還是有限。之前見了很多中國創始人,我會問對方品牌的價值是什么,但很多都講不出來,所以本質上是賣貨。很多創始人會說”國潮”。但我反而覺得如果“國潮”的現象消失,中國才會出現很多具有普世性且獨特的品牌。國潮是利用了國家想像這一個免費的IP,并不要求創始人的原創,國家會每年投入很多錢去維護和建構它。
但我相信國家文化本身是多樣化的,而消費品的價值則更是多樣化的。如果“國潮”熱度消退,每個品牌開始找到自己獨特的價值主張,中國就會是一個品牌開始出現勢能的國家。中國上一代人是“蓄電”的一代,下一代人將會是“發電”的一代,這并不會太遙遠,甚至說已經開始了。
Luke:國潮現在大家還是以“紅色“內容為主。但是何謂“國”何為“潮”呢?只有當品牌去發掘一些只有中國才有的特點,才能實現國潮的identity。元素的單純羅列不會有炸裂般的創造,鏈接在一起組成一群人的共同認知才會有“潮”。或者說我們在文化上找到可以向外輸出的元素,并咀嚼揉搓成一個好的故事的時候,才是中國有品牌有國潮的時候。我在日本倒是看見有人穿漢服的。
東子:漢服,我覺得是中國Z時代的潮牌,是基于現代媒體擬像(simulation)誕生的“被創造的傳統”。它背后有一個雙重結構,一是通過中國化符號差異化中國上一代人,二是通過中國化符號差異與歐美文化的霸權。但它也有可能是某個人群在特定人生階段的需求,希望通過符號來填補自我意識。未來,漢服能否作為一個代表中國的高品質服飾,我認為有潛力,但現在還看不到。
明亮公司主編:有什么日本的品牌在中國有機會實現更大的增長?
東子:挖一挖還有很多,但在中國做增長,肯定不能讓日本人來執行。日本的大企業沒有創新精神和組織柔軟度,能做決策的高管很多都是快退休的員工,面臨怎么退出的問題,從員工開始熬,終于熬到當老大。當他們掌權時,腦子都是想如何規避風險,順利退休。
Luke: 前幾年有日本酒日本牛肉相關的品牌融資進出中國,從結論上來說他們是掙錢的生意,但是他們不是攪動中國市場的生意。在中國的進出的日本品牌成功的無外乎注重“大局”,對主流人群主流需求給出主流解決方案。而日本酒日本牛肉終歸是小眾化的個性化的需求,從階段上來說和中國人群的契合程度還沒有那么高。雖然個性化是這兩年消費者蛻變的一個關鍵詞,但是有許多并不在網上表達意見的沉默的大多數,對于最符合他們對日本期許的商品,或許才會有機會實現大的增長。
明亮公司主編:那現有日本強勁的品牌靠什么支撐?如何面對涌出來的新品牌?
東子:購買慣性以及整個零售的生態結構。一是消費者對大品牌有信賴,容忍度高。另一方面,商社、供應商、品牌、渠道,這一系列的生態維護著日本市場的高級集中度,很難有新品牌切入的機會。日本這個社會是個人不強,體系強。體現能少讓企業犯錯,反過來,也意味著不能特別快地增長,因為他不敢犯錯,創新的動力可能會差一些。
Luke:體系能力是一個關鍵的點。日本企業的協同以及品牌的整體性做的很好(這并不同于效率高)。一個品牌通常有清晰的故事(同樣這樣的故事并不一定中國人都買賬),在執行市場營銷時有成熟的方法論和社會分銷,所以強品牌是一直可以很好地觸達到人群,獲得消費者洞察后忠誠地改善至消費者滿意的程度,以此維持強者恒強的局勢。但是如東子所說,因為他們不敢犯錯,導致微型創新/垂直領域創新很多,跳躍式的創新很少。強品牌方對于新品牌有危機感,但是也并不像故事里所寫的那樣脆弱得不堪一擊,他們都謹慎地學習模仿新產品,尋找機會投資/并購,擴大自己的商業版圖。
然而也許當日本出現“日本版拼多多”或者“日本版SHEIN”這樣的挑戰者時,格局又會變得不一樣了。
明亮公司主編:好的,謝謝兩位,我們這次先聊到這兒。在東京奧運會結束后,我們可以再探討下日本體育品牌的增長和數字化營銷。
以上就是關于pos機銷售渠道,日本零售數字化為何仍靠POS機體系的知識,后面我們會繼續為大家整理關于pos機銷售渠道的知識,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